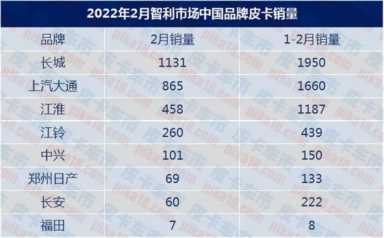家庭合影,站在中间的孩子是我
冯时林,1953年9月出生,1969年入伍;
浙江大学化工系化机专业毕业,研究员;
曾任浙江大学保卫部长,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
现为量大校友总会会长,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现代科技学院董事长。我出生在抗美援朝时期,2岁,一次严重的肺炎,差点夺走我的生命。
有人说,放弃吧,这孩子救不回来了。但父亲不肯,是他全力以赴的救治,将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所有人都说,这是个奇迹。
小时候,父亲终日忙碌,鲜少在家。成年后的我,才逐渐揭开了关于父亲的秘密:
五岁丧父,跟着母亲逃跑;年少离家学艺,独自闯荡江湖;战火纷飞中,他提起药箱就跟着中共地下党走了……
越是深入挖掘,我越是被一次次震撼。平日里低调少言的父亲,一生中竟有过这种种坎坷与传奇……
01 “阿毛,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父亲年轻时
父亲生于1921年,姓冯,名少卿,字庆生,但其实我祖上姓“章”。
何故改名换姓?这还要从遥远的十九世纪初说起。
浙东会稽山腹地,有一个群山环抱的王坛镇。离镇子八里地,有个傅家岙村
村里有个寻常农户章家,章老太五十多岁,身体健朗,却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模样。
大儿子叫章润龙,三十岁还未定亲,介绍了许多大姑娘,他都看不上。二儿子章润虎,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是个“拐脚”,走路一瘸一拐。

傅家岙村
这一天,章润龙穿了一身新衣裳,要去亲戚家做客。
他步行十几公里,有些口渴,恰好遇到一口水井。此时正值冬天,井口还冒着白气。他打上一桶水,咕嘟咕嘟喝了一气。
“喝冷水对侬(你)身体不好。”身后响起一个好听的声音。
他一回头,是一个婷婷袅袅的姑娘,面容俏丽,眼睛细长明媚,穿一件红色的棉衣,大约十七八岁,端着一盆蔬菜,笑脸盈盈地对他说。
章润龙浑身拘束起来,挠了挠头:“伢拉(我们)不讲究这些。”但他心头一动。
巧的是,章润龙在亲戚家做客时,又看见了那个姑娘。
她就住在旁边,勤快地忙里忙外,可他不敢去搭话,就远远地看着。
章润龙的表弟看到了,就说:“那是徐杏林,今年十八了,还没有婆家呢。”
说完,又别有深意地看了章润龙一眼:“侬想讨她做老嬷(老婆)?”这倒把章润龙闹了个大红脸。
郎有情妾有意,两家长辈一撮合,这门亲事水到渠成。
第二年,也就是1921年,便诞下一个男孩,取名章继德,小名阿毛。
这个阿毛,就是我的父亲。而章润龙与徐杏林,便是我的爷爷奶奶。
父亲被章家视为掌中宝,家庭虽不富裕,但也还算殷实无忧。
可这美满惬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爷爷章润龙突然得了肺痨。
家中生了变故,年幼的父亲忽然变得懂事了。父亲每日在爷爷床前服侍端药,穿梭在弥漫着浓浓中药味的房间里。
192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爷爷去世了。这一年,父亲五岁。
奶奶日日以泪洗面,为爷爷准备后事。但三七刚过,太婆便动了别的心思——要将奶奶许配给二爷爷章润虎。
得到太公太婆的应允,二爷爷喜上眉梢,一瘸一拐地推门进入奶奶的卧房,一边说话一边就伸手要搂。
奶奶忍无可忍,将二爷爷赶出了房门。奶奶打定了主意,要带父亲离开章家。
奶奶将熟睡的父亲摇醒,十分严肃地对他说:“阿毛,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要带阿毛到哪里玩呀?”
“不是玩呀,孩子。侬爹爹不在了,爷爷奶奶逼我嫁给侬二叔,我不愿意。我们离开这里去其他地方好不好?”
“我听姆妈(妈妈)的话。姆妈去哪里我也去哪里!”
“离开这里我们就要去过苦日子,吃不饱,穿不暖,侬怕不怕?”
“我不怕!跟着姆妈,我什么都不怕!”
“好,那我们今晚就走。”
奶奶立即简单收拾了几件衣裳,打成一个包裹,塞了一点干粮和盘缠,趁着夜色,带着父亲逃离了傅家岙……
02“阿毛,你现在姓冯,名叫少卿”

绍兴蕺山老街
母子二人风餐露宿,逃到绍兴城里。逃跑途中,年幼的父亲受了凉,伤风感冒,高烧不退。
“阿毛,姆妈对不住侬啊……”她抱着虚弱的父亲,挨家挨户地去打听医馆。
一些大医馆奶奶不敢进,怕付不起药钱。在好心人的引荐下,她在绍兴双井头(现称蕺山街道)找到一位叫冯顺甫的医生,听说他出自医生世家,人品极好。
这天,冯医生从邻村接诊回来,刚走到双井头,就有邻居对他说:“有个外地小老妊(少妇),带着个生病的小老倌(男孩),正在侬家门口等着看病呢。”
冯顺甫医生当即提起长衫衣摆,抄了近路,穿过一条便捷的小巷,一出巷口,就看见了坐在医馆门前台阶上的奶奶。
将母子让进屋后,经过一番望闻问切,他心中有了底,抬头说:“孩子并无大碍,只是受了些风寒;不过,孩子年幼体弱,需要调养几日。”
奶奶顿时安心不少,连连向冯医生道谢。冯顺甫医生开了方子,给我父亲服用。
眼见这对落难的母子孤苦无依,冯医生心中不免恻然,不但免去了医药费,还让母子二人暂时住在他家的柴房里。
在冯顺甫医生的精心调理下,父亲渐渐痊愈。
这些日子里,奶奶早出晚归,在附近大户人家做帮佣,努力挣钱。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冯顺甫医生和奶奶的感情悄然起了变化……
有一天,奶奶觉得口渴,但暖水瓶里却没有水了。她走到冯家院子里,见水缸里水很清澈,便舀了半瓢。
刚要喝,却听身后响起冯医生的声音:“喝冷水对侬身体不好。”
奶奶一回头,看见冯医生望着她,眼睛里溢满关爱。她想起与爷爷第一次见面时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喝冷水对侬身体不好”。
而眼前的冯医生,此刻说出了她曾对爷爷说过的话,几乎是同样的语气、同样的眼神、同样的关爱。
“侬到堂屋里来吧,有开水的。”
奶奶深情地望了冯医生一眼:“嗯呐。”
冯顺甫医生刚过不惑之年,常年走街串巷,四处行医,未及考虑婚娶,还是个单身汉。
奶奶则刚刚二十出头,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都心生爱慕之意。
在左邻右舍的撮合下,两人都觉得对方合适,便结婚了。
从此冯顺甫医生正式成了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改名“少卿”。
改名以后,奶奶对父亲说:“阿毛,侬要记住,侬现在姓冯,爹爹是冯顺甫;侬的名字,叫冯少卿,又名庆生。”
“我记住了,姆妈。”
03“爹爹,我想像您一样,做个好医生”
父亲八岁读私塾,五年的学习经历为他后来从医打下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有钟繇之风,朴素自然、平淡率真。
爷爷奶奶平常积德行善,仁术救人。从小父亲帮爷爷打下手,对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暗暗记下了许多医学知识,熟知了很多药材的名字和功效,有时还会偷偷翻看爷爷的医书,觉得其中有无限的乐趣。
父亲知道当年自己的生父死于痨病,如果当时有个好医生,就可能不致于早逝。
一个冬日,他告诉了爷爷自己的理想:“爹爹,我想像您一样,做个好医生。”爷爷很欣慰,冯家的医术终于后继有人了。
1937年,父亲16岁,开始正式系统地跟着爷爷学习中医,眷抄药方。
爷爷先把常用的处方仔细讲给父亲听,重点讲解了两百余种常见中草药的特质,从药名、外形、药用价值、药效,到用法用量、禁忌、副作用等等,讲得十分详尽。
这么多内容灌入父亲的耳朵,让他应接不暇。于是他下起苦功,起床时背,吃饭时背,连睡觉时说梦话,也时不时蹦出几个草药名来。
爷爷时不时要抽查,看到父亲都能对答如流,十分满意。于是,爷爷准备传授冯家祖传的针灸和膏药熬制法。
传说三皇五帝时期,神农帝“尝百药而制九针”,发明了针灸。后世将针灸分为针法和灸法,而爷爷尤为擅长针法。
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中,父亲渐渐掌握了中医针法,包括银针的下针、留针、转动、提针等,还将人体361个穴位记得滚瓜烂熟。
接下来,是学习膏药制作。熬膏药并不容易,熬制的火候必须掌握好,过火会焦,火候不到则熬不出汁来。
爷爷要求我父亲背诵熬膏药的一套歌诀:“一丹二油,膏药呈稠,三上三下,熬枯去渣,滴水成珠,离火下丹,丹熟造化,冷水地下,其形黑似漆,热则软,凉则硬,贴之即黏,拔之即起。”
几年下来,父亲已娴熟地掌握了冯家祖传的医术,爷爷打心眼里高兴。
“少卿的医术大有进步,甚至比我还要厉害了。”爷爷和奶奶絮叨着。
此时,爷爷已下定决心,给父亲找一位更厉害的老师,助他更上一层楼。
04 拜入“浙东大力士”叶家班门下
叶桂芳,上虞小越镇五车堰人,是浙东地区赫赫有名的游医,擅长跌打刀伤、正骨接骨、气功疗伤、拔牙镶牙,是一个全科大夫。
他品行孤傲、医术精湛、救死扶伤、行侠仗义,在宁波、绍兴一带被民间称为“浙东大力士”,名声极好。
叶桂芳医师有一个行医班子,人称“叶家班”。
叶师傅四处行医,路途中遇到些孤苦无依的孩子,便会收为学徒。班子里的徒弟们各有所长,因此“叶家班”也是个集百般武艺于一体的功夫班子。
“叶家班”里功夫最好的,是王锦彪、毛蓓成和叶桂英三人。
王锦彪,体格强壮,习武多年,有着扎实的功夫底子,能轻松举起两三百斤的石担,他的拳法也相当了得。
毛蓓成擅长气功,胸口碎大石是一绝。
叶师傅的妹妹叶桂英(化名),斗笠长袍,腰佩长剑,一身英气,她随兄行走江湖,颇具英雄气概。
叶桂英一米六七的个头,人生得标致俏丽,练得一手好拳、好剑,尤擅轻功。
“叶家班”行走江湖,主要走水路,他们开着一艘可容二三十人的大船,桅杆上悬着面红绸烫金大旗,旗上赫然题着“大力士叶桂芳”六个大字,过往行人、船只无不驻足观看。
叶师傅调教的徒弟们不但武功了得,而且医术过人,因此在宁波、绍兴一带声名远播。
爷爷看中的正是叶师傅超群的医术和行走江湖的经验,他想让父亲拜在叶师傅门下。
叶师傅也知道爷爷是个好医师,两人见面后交谈甚欢,当即便答应收父亲为徒。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爷爷便领着父亲,坐船来到五车堰拜师。
叶家大院院门早已敞开,叶师傅先在祖师爷孙思邈画像前点了香烛,父亲跪在蒲团上,对着画像三叩首,再对着叶师傅和师娘拜了三拜,敬了茶。
从此,父亲正式成为了“叶家班”的一员,开始了离家学艺的生活。
叶师傅对父亲倾囊相授。父亲年纪虽小,但聪明伶俐、为人谦逊、领悟能力又强,很讨叶师傅和师娘的喜欢。
他们年近半百,却膝下无子,商量后决定将父亲收为义子。
说来也巧,自从叶师傅认了义子,夫妇俩心情大悦,接连添了五个子女。按年龄父亲排行老大,叶家的孩子都亲切地喊他“阿毛哥”。
“叶家班”除了在叶家大院练功、学医、坐诊外,也经常去浙东几个市县行医。

每年到了赶庙会的日子,“叶家班”的队伍浩浩荡荡从船上下来,人们争相围观,热烈欢迎,颇为壮观。
十年间,父亲随着“叶家班”走南闯北,对乡野疑难杂症了解了不少,更重要的是,他的医术深得义父叶桂芳真传。
此时,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被浙东人民尊称一声“毛医生”。
05 中共地下党说:带上药具,现在就跟我走

三五支队
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浙江地区发动“宁绍战役”,浙东人民没有屈服于日军的枪炮,展开了顽强斗争。
当地抗日名气最大的当属“三五支队”。“三五支队”的全称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
“三五支队”的抗日活动深得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并迅速发展成为以四明山为根据地的游击纵队。
随着“宁绍战役”进入尾声,很多负伤的战士暂时留在地下交通员施锦槐家中养伤。
施锦槐家是泗门镇的“红色堡垒户”,他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全力安顿、保护和救治伤员。
同时,他开始秘密寻找附近的中医师傅,很快就有人向他推荐了父亲“毛医生”。
此时父亲已成为“叶家班”医术最好的医师。
施锦槐向中共地下党黄明汇报了父亲的情况后,黄明主动找到了父亲,说:“毛医生,听说侬医术很高。我们是‘三五支队’的,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现在要求助侬了。”
“我不姓毛。我姓冯,叫冯少卿。早就听说过‘三五支队’,侬抗日都是好样的,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就是。”
“那太好了。侬带上药具,现在就跟我走啊。”
“救治抗日伤员,我没有二话。”父亲备齐药品,背上药箱,按黄明的要求赶赴伤员驻点,开始救治伤员。
他正值青壮年,虽未参军上阵杀敌,也怀有一腔报国志。但是治疗枪伤,对父亲来说也是首次。
枪伤属于易感染创伤,父亲细心地给伤员消毒,在碎肉中找到子弹或炮弹碎片,小心翼翼地取出来,然后细心谨慎地缝合伤口,再上药包扎。
整个过程中,父亲想方设法减轻伤者痛苦。

父亲看着送过来的一批批伤员,心里又疼又急,但手术却一丝不苟,一例一例地做,术后每天还要观察他们的康复情况,并做好记录。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休息。
在父亲的精心医治和调理下,一些伤员的病情很快好转,恢复情况良好。父亲的医术医德,受到了伤员们和支队首长的赞赏。
06“小林病重,速归!”
1949年5月22日,余姚市解放,人民欢腾。

此时,父亲与母亲谢梅琴已结婚两年。
父亲在余姚临山镇上开了一家诊所。遇到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患者,父亲总是给予减免。
对于那些行走不便的病人,或者生了急病的,父亲总是急病人所急,亲自上门诊疗。
父亲的医术仁心大受老百姓的赞扬,当地传起了这样一句民谣:“西边有个张阿耀,东边有个冯阿毛。”
渐渐的,在山清水秀的浙东地区,“毛医生”的名气越来越大。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家里的生活也开始动荡起来。

抗美援朝时期,妇女纳鞋底赶军鞋
母亲因为女红做得好,被拉去纳鞋底,赶做军鞋。
父亲和医学界的同仁,在泗门镇中心医院李家骥带领下,上街开展义诊,所得款项全部交给镇政府。
外公也变卖了财产,把钱捐给国家。
这两三年间,家里的日子只能勉强维系,大家心里都期盼着抗美援朝的胜利。
我的姐姐阿娟,也在这期间,因为感染麻疹引起肺炎并发症,不幸天折了,年仅八岁。
国家动荡,父母舍小家为大家,终日奔波忙碌,这已是父母失去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身心都备受打击。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当父亲回家把抗美援朝胜利的消息告诉我母亲时,她十分激动。她对父亲说:“少卿啊,胜利了,咱们的孩子也快出生了。”
在欢庆抗美援朝胜利的喜庆氛围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1953年9月27日,我出生了,成为了家里第二个儿子。
母亲在妊娠期,天天为远在朝鲜的前方将士纳鞋底、做军鞋,吃得不好,营养跟不上。
因此,我从小体弱多病,经常发烧,还伴有惊厥。
1955年的夏秋之交,2岁的我不幸得了肺炎,病越来越重……
父亲正在小曹娥-朗海乡中西医联合诊所做负责人。母亲不愿打扰他工作,托人打过一次电话,恰逢父亲巡诊没接到,也就没再联系。
后来看见我一直咳嗽不止,且声音异常,情况危急之下,母亲才给父亲发了电报——“小林病重,速归!”
父亲第一时间赶回泗门镇家里,对我做了细致的检查。他先用中医方法作了初步诊治,但我的病情不见好转。
慢慢地,我开始眼睛凹陷,双目无光,脉相不健,连呼吸也变得困难,常常陷入深度昏迷。
身边人看了我病情危重的样子,纷纷劝父亲说:“毛医生,看来孩子是救不过来了,放弃吧。”
面对七嘴八舌的规劝,父亲只回答了一个字:“不!”
他只身跑到余姚县医院求助,请来医生们到泗门镇家里,一起参与对我的抢救。
然而,几位医生联合诊断后,都认为情况很不乐观。父亲与众医生商量,最后决定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案治疗。
我被注射了超剂量青链霉素,那是县医院的医生带来的特效药。同时,我还服用了父亲自己动手熬制的祖传中药汤剂。
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慢慢的,我的呼吸变得平顺了,均匀了。父亲又给我把了脉,量了体温,对着几个医生点了点头。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父亲对县医院赶来抢救我的医生表示了感谢,送他们出镇后,又赶紧返回来,坐到了我的病床前。
在抢救我的日子里,父母几天几夜守在我身旁,看顾和照料我。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鬼门关转了转,又折返回来了。
当我不再昏睡并睁开眼睛时,母亲高兴得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叫道:“少卿少卿,小林醒了,小林醒了,救回来啦!”
父亲激动地紧紧捏着母亲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好一会儿才放松下来,长长舒了一口气,看看我,又看看母亲,这才低下头,擦擦自己湿润的眼睛说:“善哉,善哉。”
左邻右舍都说,我被救回来,是个奇迹。
不久后,父亲向上级辞去了小曹娥-朗海乡中西医联合诊所负责人的职务,决定回到泗门镇老家,区里让他负责建立泗门镇第二高级社保健站。
对父亲来说,已经失去太多了,能陪伴在至亲至爱之人的身边,才是最重要的吧。
但时代的滚滚浪潮,又推着他不得不一次次远行……
07 一句“试试看”,便干了33年
1958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家里来了两位重要的客人,泗门区委副书记干志成和泗门区中心医院院长李家骥。
干书记说:“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区委决定动员有医疗工作经验的私人诊所医生,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建立卫生所、保健院,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
父亲听明白了,区委的意思是让他再度出山,到湖北公社去开创新的集体医疗卫生事业。
“感谢组织信任。”父亲对干书记和李院长表态说,“我试试看。”
母亲正怀着三弟,照顾不过来,五岁的我便要跟着父亲一起去湖北公社。
湖北公社距家有七八公里地,如果不走小路,只能坐船前去。陪父亲出任保健所所长的这天,是我第一次坐船。
保健所东西朝向,西门连着应家的院子,一出门有个烧饭烧水的地方,东门为正门,有两级台阶,就这么简简单单。
房子四周,种满了凤仙花和鸡冠花,煞是好看。经过几个月的筹建,保健所基本就绪。
挂牌仪式当天,在一阵鞭炮声后,公社党委书记宋天生宣布:“湖北公社保健所今天正式挂牌成立!咱们以后,也有了自己的保健所啦!”
父亲也没想到,自己竟把大半生的热血,都投进了这湖北公社。
就是这一句“试试看”,让父亲一干便是28年,直到退休,又返聘了5年。

如今的绍兴卫校
保健所成立不久后,父亲被派到绍兴卫生学校学习西医知识,三个月的培训时间,父亲掌握了更多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
为了改变乡村缺医少药的情况,1963年6月,父亲又动脑筋,想办法,自编教材和辅导材料,组织举办了湖北公社第一期卫生员培训班。
经过将近半年的学习,学员们从父亲的培训班“毕业”了。从此,公社各村的社员们,都有了自己的“医生”。一些常见的疾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

上世纪农村的“赤脚医生”
母亲也在父亲的建议下,参加了慈溪县沈师桥妇科助产士培训班,刻苦学习,成为了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妇幼天使”。
父母亲在保健所里建起了第一个分娩室和妇科门诊,为公社的妇女们提供了生育和卫生保障。
不仅如此,父亲还在深入农村基层行医问诊、救死扶伤的路上,创造了一个个传奇……
08 凌晨,他喝下半瓶剧毒农药“1059”
这一天,天蒙蒙亮,窗外就下起了小雨。
母亲总是第一个起床,自己洗漱完了,就忙着烧水,做早饭。
我还赖在床上。突然,医院大门外面传来了急促的呼救声:“冯院长!冯师母!侬可要救救伢儿子啊!”
我凝神谛听,又听到撕心裂肺的声音:“志尧啊,侬为什么会想不通,为什么要喝农药啊……”
嘈杂的喊声,让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跑到医院门口。
只见四个年轻人,抬着一扇门板做成的简易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年轻人,后面哭着喊着的,是他的母亲。
父亲脸都没有顾得上洗,赶紧一边接诊,一边询问病人的情况。
原来,湖北公社七大队的王志尧和六大队的胡淑芬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两年多的恋情使他们如胶似漆,难分难舍,谁都不愿意离开对方。
王志尧的母亲说,昨晚她儿子去胡淑芬家里提亲,不料被她的父亲奚落了一番。
“人模狗样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胡淑芬的父亲说,“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侬介般配啷格?”
王志尧回到家里,整个晚上都在抽烟。到了凌晨,他把一瓶剧毒农药“1059”喝下半瓶,对家里人说,反正娶不到淑芬,他也不想活了。
王志尧服毒自杀,当时已经面色发紫,口吐白沫,神志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我父亲问明情况后,立即指挥医护人员救治,并快速作了分工:
母亲和静芝医师用温肥皂水为患者灌服洗胃;将高锰酸钾用水溶解配比,给患者灌肠,并马上对病人注射了阿托品和解磷定、氯磷定、生理盐水溶液。
鉴于人手紧张,我父亲又调来五位“赤脚医生”到公社卫生院集合,组成临时抢救小组,自任组长,展开了紧张的救治。
24小时过去了,病人生命体征逐渐有了改善。
虽然母亲和几位“赤脚医生”戴了口罩,也采取了一定防护措施,患者的呕吐物和排泄物还是使他们产生了轻度中毒症状。
父亲随后又对母亲和几位“赤脚医生”做了简单治疗。
“1059”属剧毒农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棉区都有使用,但七十年代后期,已经严禁使用。
喝“1059”剧毒农药自杀的患者,在父亲负责的湖北公社医院,还是第一次碰到。
父亲坚持中西医结合,一方面注射大剂量的阿托品、解磷定,另一方面使用中草药配合治疗,用绿豆、甘草、曼陀罗、金鸡尾、金银花煎服排毒。
72小时过去了,经过抢救小组的全力施救,王志尧体内排出了十几条蛔虫,可见剧毒农药“1059”的毒性之强。
患者脱毒了,生命体征大为好转,但是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却一个个累得直不起腰来,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
“谢谢,谢谢。”父亲一边捶着后腰,一边轻声说,“脱离危险了,侬都去休息吧,这里有我。”可大家围着父亲,久久不愿意离去。
72小时的危险期终于熬过去了,众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喝“1059”自杀的患者病愈出院了,我父亲却添上了一桩新的心事,就是王志尧和胡淑芬的婚事。
他了解到两个年轻人自由恋爱两年多,感情纯洁,心心相印,只因为王志尧家庭经济条件比胡淑芬家差,男方才被女方父亲嫌弃。
我父亲心地善良,很想玉成良缘,便生出了“帮人帮到底”的想法。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父亲登门拜访了胡淑芬的父亲胡大伯。经过一番循循善诱,他娓娓道来:
“胡老哥,依选女婿,首先是看人品,人品好是第一位的。其次,是看双方有没有感情。感情好,孩子们能互相恩爱,这才是建立家庭最大的保障。”
经过父亲的劝导,胡家最终答应了亲事。王志尧和胡淑芬有情人终成眷属,花好月圆,喜结连理。
婚礼上,父亲在大家不断的敬酒中,喝多了。他平日里有五斤黄酒的量,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第一次喝醉。
许是真的高兴吧,他不仅成功救治了生命垂危的王志尧,还玉成了他和胡淑芬的美满姻缘。
09 “瘟神”来了,十有九户绝后代
1963年秋天,“瘟神”猝不及防地来了。
民间曾经流传过这样的歌谣: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

血吸虫病患者
五六十年代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广泛,涉及12个省市,350个县市,患病人数高达1000多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
它传染性极强,据浙江省调查统计,当时病区每年新增患者近10%,许多人在水稻田劳作时,不知不觉就感染了。
在病害严重的地区,出现整村人口死亡的情况。这病不仅害人,也急速降低着全国的生育率。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治灭血吸虫病。”具体来说,便是从源头上消灭钉螺,从水草、粪便中消灭虫卵。

那时我只有十二三岁。暑假时,我帮助区防疫站的同志去杭州湾水塘,抽水样送到防疫站化验。结果显示,当地病源与乡村厕所是强相关的关系。
父亲作为湖北公社保健所所长便提议全公社开展大规模的改水、改厕运动,以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公社还经常性派专业人员为大队居民房前屋后的粪缸灭蚊、灭蝇,后来又提倡改建饮水池和水冲式坐便器。
与湖北公社距离不远的慈溪县泗门区海南村,是重灾区。
慈溪县的县委书记黄建英,带领县级机关和卫生局“血防”领导小组,在海南村召开了县、区、公社三级卫生医疗工作人员现场会,我父亲也参加了。
会后,黄书记握着父亲的手说:“侬就是冯医师,祖传中医,是乡村卫生医疗事业的拓流者,很了不起!中医博大精深,民间有很多神奇的草药和秘方,还请冯医师为‘血防’工作多做贡献啊。”
这话一直在父亲耳旁萦绕,他牢记黄书记对他的嘱托,在治疗“血吸虫病”工作中发挥中医优势。
他翻阅了大量祖传的土剂良方,终于寻找到中草药治疗“大肚子病”的方法。
父亲先是用腹水草消肿积水、攻痞块、扶正气、除虫毒,自制了中药配方“腹水散灭虫剂”,并谨慎地应用于临床。
他后来又用甘草、金银花、黄连、青皮、原木子、草果、柴胡、黄芩、茯苓、栀子和半夏等进行清热化湿,并亲自煎药,配制“清垫理脾驱虫汤”杀虫。
这些中医药的方法都取得了良好效果,经父亲治疗过的十几位病人都痊愈出院,并且没有发生任何后遗症。
在1965和1966年,父亲先后参加县卫生局抽调的两个批次医疗工作者队伍,历时三个多月,全面普查钉螺状况,强化管理水源和人畜粪便,收到的成效是良好的。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战胜血吸虫病以后,杭州湾地区慈溪县又发生了严重的“二号病”——霍乱疫情。
父亲曾告诉我,这次疫情的发生,让他遭遇到了自己的一件终生憾事。
10 “你胆子这么大,公社书记的事也敢管?”
父亲是湖北公社卫生院院长,作为一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民间中医,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全科医生。
1963年底,公社党委书记沈海标找父亲谈话,肯定了父亲所做的贡献,并希望他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
这次谈话后,父亲激动了好长时间,他用了几个夜晚,认真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郑重地给了党组织。
他表示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为农村医疗事业贡献毕生的力量,为党和政府的卫生事业奋斗终身。
但是,令父亲始料未及的是,入党申请提交后,公社党委主要领导却发生了人事变动,宋天生和沈海标书记都调到另外的公社任职去了。
与此同时,大杭州湾地区的慈溪县又发生了严重的“二号病”疫情。

“二号病”也叫霍乱,当地老百姓叫它“瘪螺痧”,传染性极强,主要症状为无发热、无痛腹泻、呕吐,严重时可致人死亡。
这次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发病人数之多、疫情势头之猛,都为历史罕见。仅发病死亡的人数,在全国便多达三万余人。
查明杭州湾一带的病人多为吃了不卫生的海产品,政府专门发出“政府令”:严令禁止吃泥螺和醉蟹,严防、严控“二号病”蔓延。
父亲作为卫生院院长,责无旁贷要查验市场销售情况,对泥螺、沙蟹等海产食品严格管控。
有一天,父亲到书记办公室汇报工作,发现湖北公社新任党委书记居然违背政府禁令,食用泥螺。
父亲便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他:“书记,侬为啥要吃泥螺,不按规定和要求做?”
新书记见父亲口吻严肃,有些下不来台,悻悻地说:“吃口泥螺,有什么大不了?”
“可侬是书记啊,”父亲寸步不让,“侬带头吃这些东西,如果别人有样学样,我们该怎么管控?”
“让侬管控别人,侬还管到我头上来了?”书记更加不高兴了,“我吃死了,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要侬管!”
“这可不是侬自己的事情,书记。既然我们卫生院做防控‘二号病’工作,就一定得管到侬头上。”
父亲说完,也不管书记怎么争辩,拿起他面前装泥螺的盘子,走到厕所里把泥螺倒掉了。
书记跟着追了几步,又觉得不妥,退回了办公室。他十分恼怒,觉得父亲小题大做,是故意让他为难,不给他面子。
父亲拿着空盘子回到书记办公室,想继续汇报工作。
“侬瞧瞧侬,干嗦格来?”书记站在办公桌后面,见父亲进去,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侬冯少卿眼里,还有我这个书记吗?”
“我眼里当然有侬这个书记。”父亲平静地说,“这不是正要向侬汇报工作嘛。”
“侬冯少卿胆子这么大,连我公社书记的事也敢管!”他不接父亲的话,生气地说道,“侬还想不想入党了?”
“我冯少卿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决不把党和政府的指令当儿戏!我宁可不入,也要按党和政府的指示办!”
因为这次冲突,父亲入党的问题便一直被搁置下来。
这位书记作为公社一把手,公报私仇,在党委会上恨恨地说:“冯少卿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根本不把我们党委放眼里!”
见会上没人站出来为我父亲说话,书记最后总结道:“让这样的人入了党,还了得?”
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不让我父亲入党。这次党委会的“会议纪要”写道:冯少卿入党问题,不予讨论,不予复议。
最终,父亲没有能够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这成了他这一生的憾事。
11 “少卿,撑不住了,就先歇息下来吧。”
六十年代,农村医疗刚刚起步,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建设。而在这多灾多难,看天吃饭的稻田间,父亲始终如一,扎根基层。
1966年秋,慈溪县湖北公社暴发了流行性脑膜炎。
老百姓人心惶惶,病人一批一批往公社卫生院送。但卫生院人手很紧,正式的医生只有我父亲和另外两个做普通医护工作的。
这段时间里,父亲他们又做医生又做护士,夜以继日坚守岗位,抢救治愈了大量病人。
但是他已经疲劳至极,走路时感觉头重脚轻,累得随时可能瘫倒在地。
“少卿,”我母亲劝他,“撑不住了,就先歇息下来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农药中毒事件又频繁发生。
喝剧毒农药“1059”自杀的王志尧救回来之后,又有许多农民在灌溉农药期间不慎吸入中毒,有时中毒者甚至一批一批前来就诊。
特别是傍晚时分,从田里送来的中毒病人更是又急又重,眼看着就命悬一线。
“救人啊,救人啊!”送医的老乡大多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也有的惊慌失措,哭声连连。
不管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来就诊,只要病人一到,父亲总是一马当先,从不计较自己的休息时间。

父亲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他是个善于思考、勤于调查研究和乐于想办法的人。他会从贴近农村实际的角度想出一丝新点子,做一些工作创新的尝试。
1970年,父亲在湖北公社全面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由于政策惠民合理,门诊人数骤然增加。
父亲医院的医生护士人数本来就少,工作量却骤增。一天的门诊人数,多时可达100至200人,少时,也有80至90人,有时还有加夜急诊。
连续的超负荷工作,父亲积劳成疾,患了重症肝炎,他却坚持上班。
母亲经常心疼得偷偷掉眼泪:“少卿啊,侬这样拼命工作,是要出大问题的啊。”
直到有一天,父亲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向区里请示是否可以“半工半休”。他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对自己进行肝病治疗,病情才有所好转。
父亲作为湖北公社卫生院院长,处在医疗卫生事业最基层,他对工作永远严肃认真,宵衣旰食,慎终如始。
紧接着,文革来了……父亲遭受到的屈辱和磨难层出不穷,直到退休。
12 这份内疚,伴随了父亲一生
文革期间,湖北公社革委会分管合作医疗的财务管理层,出现了贪污盗窃等违纪违规问题。
父亲为确保集体资金和老百姓的血汗钱不受损失,毅然进行了检举和揭露。
正值造反派掌权,公社革委会听信小人谗言,开始对父亲打击报复。
批斗会上,造反派头头鲁峰(化名)和一个姓金的,要我父亲下跪。
父亲坚决不从。
鲁峰大约三十几岁,腰间扎着武装带,双手叉着腰,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走到父亲身边,朝腰上猛地踹了一脚,嘴里喝道:“冯少卿,跪下!”
父亲一下子跌倒在地,但是,他又爬了起来,倔强地站着,用强硬的态度对造反派怒斥道:“侬这帮畜生,会得报应的!”
批斗会结束的当天晚上,父亲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嚎啕大哭。从不轻易流泪的他,真的伤心到了极致。母亲也跟着流着泪,只能轻声安慰和开导父亲。
这天夜里,我们兄弟几个听见父母说话说到很晚。我们都很害怕,不知道第二天,第三天和以后日子里,还会发生什么。
第二天早上,父亲发现自己尿中带血。
他担心肾被造反派踢坏,赶紧和家人告别,让母亲帮他向公社卫生院办公室打了招呼请假,自己紧急赶往杭州的王师弟家里治疗养病。
一个多月时间,父亲的尿血症状才得到改善,逐渐恢复了健康。
造反派们不仅在政治上歧视父亲,生活上虐待他,还将他每月的工资无端扣掉40元,致使我们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也是在这期间,父亲留下了第二个终身憾事。
父亲的阿姨,我的姨奶奶徐友凤,在上海沦陷时连遭不幸。
丈夫被日本人飞机投的炸弹炸死,两个儿子,一个在逃难中病死,一个饿得皮包骨头,最终因吃了泔水桶里的残羹剩饭,得了痢疾,却没钱治病,便血而亡。
姨奶奶失去了三位至亲,终日以泪洗面,多次生出自杀的念头,在街坊邻里的劝说和帮助下,艰难地活了下来。
后来姨奶奶辗转多地,来到我们家一起生活,日子虽不富裕,但也能和亲人相依为命。
文革时,父亲的工资被无故扣掉一半,家里就要揭不开锅了。
姨奶奶主动说要去公社食堂打工,补贴家用。她很珍惜这份工作,兢兢业业,不敢怠慢。
革委会的人紧抓着父亲不放,要将他整倒。姨奶奶无意间听说,他们要送父亲去坐大牢,便气得冲上前去理论。
话还没说完,她就瘫倒在地上,脑中风了。
经过父亲的全力救治,姨奶奶仍然落下了半身瘫痪。母亲像照顾亲娘一般在姨奶奶床前服侍,一日三餐,喂饭喂水,擦身换洗。
1977年,在床上躺了九年多的姨奶奶,还是走了。父母将姨奶奶的骨灰与奶奶合葬,希望她们能在天堂作伴,互相关心,永不寂寞。
每当回想起姨奶奶冲进公社据理力争的事情,父亲总是后悔不已,觉得自己不该接她来此,卷入这是是非非中……
这份内疚,伴随了父亲一生。
13 “退休之前,组织上终于还了我一个清白”
1972年底,湖北公社农村合作医疗机制与公社卫生院剥离,下放到各生产大队合作医疗站,以大队为单位参保报销。
这导致老百姓不信任,合作医疗经费经常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上级处理这一问题的政策是:各自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自行淘汰。
本来势头良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仅仅运作了三至五年,便陆续停办了。
父亲负责的湖北公社卫生院是集体编制,自负盈亏,国家不给补贴。
不出所料,每天到公社卫生院看门诊的人数出现了断崖式跌落,几乎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
医院业务收入减少,员工薪资发不出来,医护人员的生活很快失去了基本保障。
父亲主持工作的公社医院,现实情况更加严峻。
他就像一位站在悬崖边上的“麦田守望者”,虽然已经身心俱疲,却以超常的毅力、坚韧的心态和负责任的精神,全力阻止着公社医院跌入深谷。
父亲一边坚持向县、地区和省行政主管部门写信,反映农村基层医卫单位情况。
一边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坚持把“老三件”的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等医疗器械作了更新。
当时国民经济在生产领域出现梗阻,物资异常紧缺。父亲便主动通过亲友关系联系资源,亲自跨县、跨地区采购物资。
他不仅拼体力、拼精力,还悄悄拿出家里多年的积蓄,为集体建设垫付急需的资金。
他坚持完善了医院的设备,在艰难困苦中让各科室医疗设施完成了升级,以一己之力创造了公社医院的奇迹。
1981年,父亲到了退休年龄。
没想到,在离任审计中,竟然有人指责父亲在医院基建中存在违纪、违规和贪污现象。
这让无辜的父亲再次蒙受冤届,身心备受推残。
被审计的日子里,父亲陷入了深深的沉默,母亲只能陪着他悄悄抹泪。
许多人气不过,为父亲鸣不平,但父亲始终保持着沉默,没有上访。
我们全家人都知道,他在等待,并且坚信,清者自清。他相信组织上经过调查,一定会给出公正结论。
最终,在各级党委和有关领导关心下,父亲的冤案得以昭雪。他非常感谢组织。
父亲一生有泪不轻弹,但是,当他拿着印有组织结论的公函来到母亲面前时,声音禁不住有些哽咽:“侬看,侬看看,退休之前,组织上终于还了我一个清白。”
母亲看了报告,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父母那一代人,是那么重视政治生命的清白,那么珍惜道德评价的公正。组织上的公正结论,再次焕发了父亲的工作热忱。
他主动申请延迟退休,自愿继续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一干就是五年。

1985年湖北公社卫生员合影,父亲在第一排左三
1986年,父亲才依依惜别了同事和他亲手打造并工作了33年的湖北公社医院,恋恋不舍地回到泗门镇的家里。
父亲办理退休手续时,他看过的病人还有1000多元医药费没有结清,他就帮忙支付了那些医药费。
每每想到父亲那几年蒙受冤屈时的忍辱负重,想到他为医院事业发展的殚精竭虑,想到他默默相信组织的无私襟怀,我都忍不住会热泪盈眶。
父亲,您太不容易,太了不起了!
14 一颗仁爱的正义之心,一生舍己为人
2008年7月25日,父亲走了,享年87岁。
父亲做了一辈子医生,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省吃俭用的他在临终时留下遗言: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捐献给湖北村的卫生事业。
为实现父亲的遗愿,我们四兄弟和村里商量以后,决定用这笔资金建造余姚泗门镇湖北社区卫生服务站。
2011年,占地200余平方米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已经落成。社区卫生站配备了7名专业医务人员,设置了处置室、全科门诊、预防保健室等。

2011年,湖北冯少卿社区卫生服务站成立
父亲从战火纷飞的旧社会,走到全面建设的新中国。多么希望父亲在天上能够看到这一切。
他以医术精湛而闻名,始终选择扎根农村,关爱着身边的每一位群众;他一生植根乡间,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困境不遗余力,救死扶伤无数。
父亲,有一颗仁爱的正义之心,一生舍己为人。
我们家在泗门镇属中医世家,父亲从爷爷那里秉承的医术仁心,又经革命战争年代的影响和淬炼,让他在家里奉行的家教和家风,都非常严正。

全家福
五岁,我跟着父亲去湖北公社建保健所,我亲眼看着父亲一日日奔波劳碌,行医救人,舍小家为大家,带病坚持工作,鲜少考虑自身。
父亲的言行给我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亦塑造了我独立而丰满的灵魂。
我出生于抗美援朝时期,1969年入伍,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7岁离家,我在福建当了七年兵。退伍回到泗门老家后,我没有放弃学习,终于考上浙江大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1978年,我从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在学校的培养和锻炼下,我不断成长,从浙大化工系团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做到浙大组织部干事,后又担任浙大派出所所长,保卫处处长。
此间,我攻读了研究生,在专业技术方面不断进步,最终晋升为研究员。
32年的浙大工作经历,我努力付出,获得了诸多荣誉,但收获最大的,是一众帮助我、支持我、指引我前进的领导和老师们。
2006年,经中共浙江省委考察研究,决定将我调入中国计量学院(后更名“中国计量大学”)担任副校长和党委委员。鉴于工作需要,组织批准我延迟至2018年退休。
这期间,我还生了一场大病,病毒性脑膜炎。幸得朋友们的热心帮助和医生们的全力救治,终于熬过来了,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退休后,我又受邀继续担任校友总会会长和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我欣然同意,很愿意继续为学校工作。
在中国计量大学,这一干就是十五年。

直到现在,我仍因工作时常忙碌奔波,但每每遇到困难,我总是会想到父亲,想到他挎着药箱,独自走在乡间的样子。
那个坚忍不拔的身影,一直鼓舞着我,激励着我。
一晃,父亲已离开13年,但在我记忆中,关于他的一切是永不褪色的,深深刻在了生命里。
今年,是父亲的一百岁诞辰。我希望他这一生的传奇故事,能为更多人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