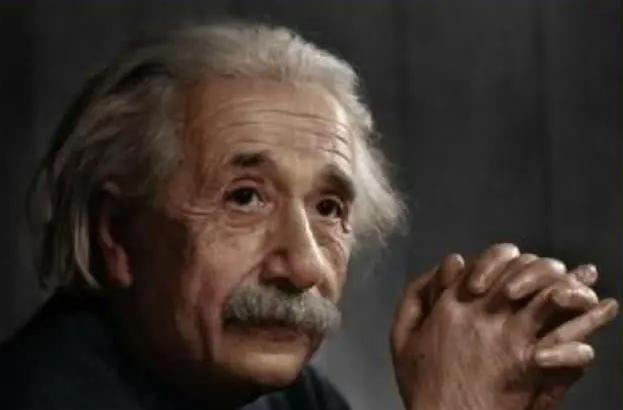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越来越多的城市正试图挤进“千万人口俱乐部”,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久前,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下称《分县资料》)公布了683个城市的人口数据。界面新闻梳理发现,常住人口在900万-1000万的城市共11个,其中有8个城市已经明确或间接提出,要将常住人口规模提升到1000万。而常住人口规模低于900万的城市中,仍有4个城市制定了人口规模扩容目标,也剑指1000万。
在老龄化、低生育率、总人口数量面临负增长的背景下,这些城市提出千万人口规模目标的动机是什么?它们又如何去完成这一目标?
谁想加入“千万人口俱乐部”?
2022年3月,浙江省温州市公布《温州市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到2025年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目标。近期,该“规划”最终版本公布,继续保留了这一目标,引发外界热议。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温州设定人口目标的衡量标准,并非指城区常住人口(又称城区人口),而是指行政辖区内的常住人口(又称常住人口)。同一地的城区人口往往比常住人口少。这也意味着,即便常住人口增加到1000万,城市级别也不能得到提升。根据《分县资料》的数据,温州市常住人口为957.29万,但城区人口仅有238.18万,为Ⅱ型大城市。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谢良兵向界面新闻介绍,通常讲的“千万级人口超大城市”指的是城区常住人口的数量,而非行政区划概念下的市域常住人口。不过,目前很多城市习惯将市域常住人口过千万当成城市能级改变的重要指标,也让“千万级人口”成为许多城市趋之若鹜的追逐目标。
“但这并不科学,只有城区人口的数量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聚集效应,而人口聚集效应带来的就是人才、科技、经济等各类资源要素的聚集。”谢良兵说。

从常住人口看,温州市以957.29万人口位列浙江省第二,紧随其后的是宁波市,常住人口为940.43万。人口和经济实力处于“伯仲之间”温州和宁波,都有冲刺1000万常住人口规模的野心,不过温州市表现得更为积极。相比之下,宁波市至今尚未公布该市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
一个城市的人口发展目标,通常在发改委起草的人口发展规划或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宁波市发改委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向界面新闻表示,宁波市人口发展规划已经在制定中,但未明确是否提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目标。该人士透露,宁波市的人口发展规划之所以没有对外公布,是希望与浙江省人口发展规划步调一致。目前,该省人口发展规划尚未公布。
不过,在2022年4月召开的宁波“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2026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2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2万元”。按此折算,到2026年,宁波市常住人口也将达到1000万。
值得注意的是,在冲刺“千万人口俱乐部”的意愿方面,省会城市似乎显现出更多焦虑。常住人口在900万-1000万的8个提出千万人口目标的城市中,有4个是省会城市,分别是南京、济南、合肥和长春。而在常住人口低于900万的城市中,4个提出千万人口规模目标的城市,也全部为省会城市,分别是昆明、南宁、福州和贵阳。
这些省会城市的“尴尬”不仅在于经济层面被周围的强邻环伺,而且常住人口往往少于省内其他非省会城市。比如,福州市常住人口是829.13万,与位列福建省常住人口第一的泉州市相差近50万;济南市常住人口为920.24万,只能位列省内第四,排在它前面的包括临沂市、青岛市和潍坊市。
作为江苏省会,南京市常住人口只有931.47万,而省内苏州市常住人口已达1274.83万,且周边的杭州市和上海市常住人口都已过千万,甚至西边邻居合肥市的常住人口也达到936.99万。为此,20222年年4月,南京市发布《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成为常住人口突破千万、经济总量突破两万亿元的超大城市。
人口资源与“强省会战略”
常住人口突破1000万,并不能像城区人口过千万一样带来规模效应,也不能提升城市级别,为何这一目标仍被十多个城市写入发展规划?
南方一位省级经济部门的官员告诉界面新闻,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只是一个意向性文件,是经济、社会等其他发展规划的依据,而非必须完成的任务。不过,近些年,体制内逐渐意识到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而GDP仍是考核官员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不少地方将吸引人才,提高人口数量纳入发展规划。
长期关注城市化的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罗淳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受“人满为患”观念影响,总是将人口作为负担看待,忽略了人口作为资源属性的一面。事实上,“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而且人一生所创造的财富总是大于他所消耗的资源。人口密度与城市经济繁荣关系密切,譬如在人口密度很高的香港和东京,都是经济繁荣的增长极或核心区,也最能吸引人口聚集。
罗淳告诉界面新闻,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态势,已经从以前的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转变到大城市化和城市集群化发展阶段,省会城市、大城市不断扩张,中小城市趋于萎缩,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城市化就是要素聚集的过程,人口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自由的环境下,“理性人”会选择“用脚投票”,迁徙到就业机会更多、生活条件更优的地方去。当代中国城镇化率的加速上升,正是乡城人口迁移的结果。
谢良兵指出,在中国现行管理体制下,认定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城市群都市圈核心城市时,人口规模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城区人口突破千万大关之后,城市的集聚效应会变得更为明显,会对各类资源产生更为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优质资源,这也会让城市在各类竞逐中占尽先机。”
而城市能级的划分对于城市在国家战略中争取更多更好的政策更加影响深远。尤其是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总量即将进入负增长的时代,城市抢占人口红利显得更为紧迫。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房地产,即所谓的土地财政,而当前房地产市场已从快速扩张的“增量市场”转向存量与增量并存,在“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人口的增量就成了地方楼市刚需和改善的重要补充,也会是地方楼市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
界面新闻注意到,“十四五”以来,许多省份制定了“强省会”战略。在现有治理模式下,省会被视为一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冲刺千万人口俱乐部的省会城市中,不少城市也制定了强省会战略。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省经济底子较为薄弱。省会贵阳市的常住人口只有598.7万,但贵阳也同样提出了一项颇具“创新”特色的人口增长计划。
2021年4月13日,贵阳市贵安新区“强省会”五年行动誓师大会召开,会议印发了《贵阳市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方案》,该方案提出,依托以贵阳贵安为中心、周边1小时通勤范围的城市组成都市圈,建设常住人口达到1000万人以上的贵阳—贵安—安顺—黔南经济区,贵阳市与周边区域统一规划、协调推进、联动发展,引领带动黔中城市群高质量打造全省核心增长极。
目前,贵阳市常住人口为598.7万人,安顺市常住人口为245.9万人,黔南州常住人口为349.6万人,这三个市域常住人口的总和已经超过1194万。
谢良兵指出,贵州省整体处于人口流出状态,比如安顺市流出人口为58.37万人,因此,贵阳提出建设常住人口达到1000万人以上的贵阳—贵安—安顺—黔南经济区,并不算脱离经济规律,而是贵阳市“强省会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目的是防止人口外流出省,将人口聚集在省内发展。
罗淳则提醒,城市化的实现并不在于人口聚集形态的空间变化,而取决于人口从业属性的非农转变,脱离了产业支撑,简单地“画大饼”,将农村人口纳入城市规划,而不去考虑他们的后续生计问题,这势必导致“半城镇化”或“病态城镇化”。
他认为,完整的城市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包括非农化和市民化在内的“三化”联动的过程,而且一个健康有序、持续深入的城市化应是即得益于非农化的支撑、又有助于市民化的实现。
城市抢人“内卷”已很严重
尚不清楚这些冲刺千万人口俱乐部的城市将出台哪些配套措施。不过从其他城市的经验来看,除了就业、创业方面的支持政策外,放宽的落户政策成为许多地方吸引人口的主要手段。这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许多大城市的购房资格与户籍挂钩。年轻人能在一个城市轻松落户,即意味着拥有了购房资格,这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较大。
罗淳指出,目前各大城市面临的人口问题,并不是规模大小的问题,而是结构优劣的问题。在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双重困境下,劳动力的短缺削弱了城市创新活力,增大了经济发展负担,近些年许多城市争相出台“抢人”政策,就是希望留住大中专毕业生,既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又增加优质劳动人口。这也是完成人口规划目标的主要对象。
“比如西安市,最早悟到了人口聚集的重要性,在‘抢人’竞赛中抢占了先机。”罗淳表示,西安高校云集,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上百万,但过去留在本市的不多,大量年轻的毕业生去了一线城市。西安出台人才新政后,这一局面明显改变。“六普”至“七普”10年间,西安市净增常住人口近450万。目前,西安的常住人口已逾千万。
但谢良兵认为,单纯的放开落户政策也并非一劳永逸。从2017年开始,西安市、武汉市等很多城市陆陆续续加入了所谓的“抢人大战”行列,其背后就是当地户籍制度的松动与逐步放开。而总市域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也想方设法在学历、社保等方面降低标准,进一步放宽落户限制。“内卷”化现象已经很严重。
他注意到,比如在天津市,因为放开了落户,常住人口从2011年开始连续五年增长,2016年更是直接增加了102万人,达到1443万人。天津还在“抢人大战”中实施了“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引进了40万人口。但也是从2016年开始,天津人口逐渐停止增长。从2016年到2021年,天津市的常住人口总量从1443万人又下降到1373万人,人口骤降了近70万人。
“也就是说,对于不少人口处于净流出的城市而言,外来人口这个增量要想做大并不容易。”谢良兵介绍,数据显示,2001年-2010年,一线、强二线、其他线城市全域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1.9%、0.6%;2011-2016年,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速分别为1.5%、1.2%、0.4%,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位于东北的长春市、沈阳市和哈尔滨市都出台了不少人口政策,落户条件接近“零门槛”,长春市和沈阳市也提出了常住人口达1000万的目标,但成效甚微。
2021年,长春市和沈阳市的常住人口分别为908.72万人、911.8万人,与2020年的数据相比,一年仅仅增加2.03万、4.97万人。而作为“东北人口第一城”的哈尔滨市,虽然常住人口很早就突破1000万,但从2017年开始人口下降,到2021年常住人口已跌破1000万。
谢良兵认为,吸引人才必须抛弃“解决户口和房子”的老旧思路,在国家发改委提出放开落户限制,人口自由迁徙日益成为现实的前提下,落户零门槛只会是各城市吸引人才的标配,难以真正成为城市吸引人才的竞争力优势。留住人才的关键在于,必须有大量合适的就业机会,否则,一波波的人才大战很可能最终沦为“抢人”,而非“抢人才”。
其次,谢良兵指出,城市要有发达的经济与产业结构。增加岗位数量、提升岗位质量,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抢人”同样离不开产业发展。从广撒网到专业化揽才,城市才能逐渐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人”,比如厦门市、南昌市,就专门聚焦到一个产业进行“人才专攻”。
此外,“有利于留住人才的‘软环境’也很重要,比如更公平、更自由、更包容的社会环境。吸引人才必须回归其本质——人才引得进来,还能留得住。”谢良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