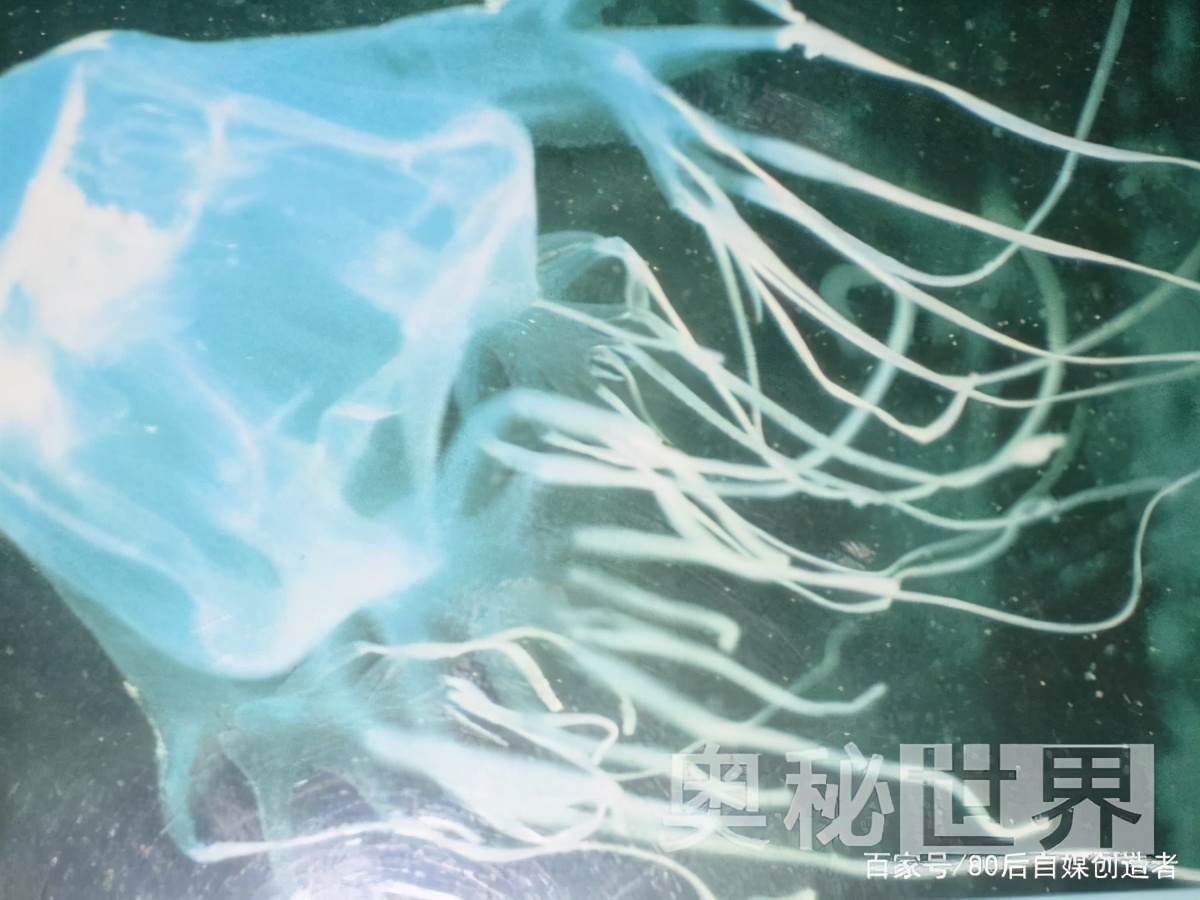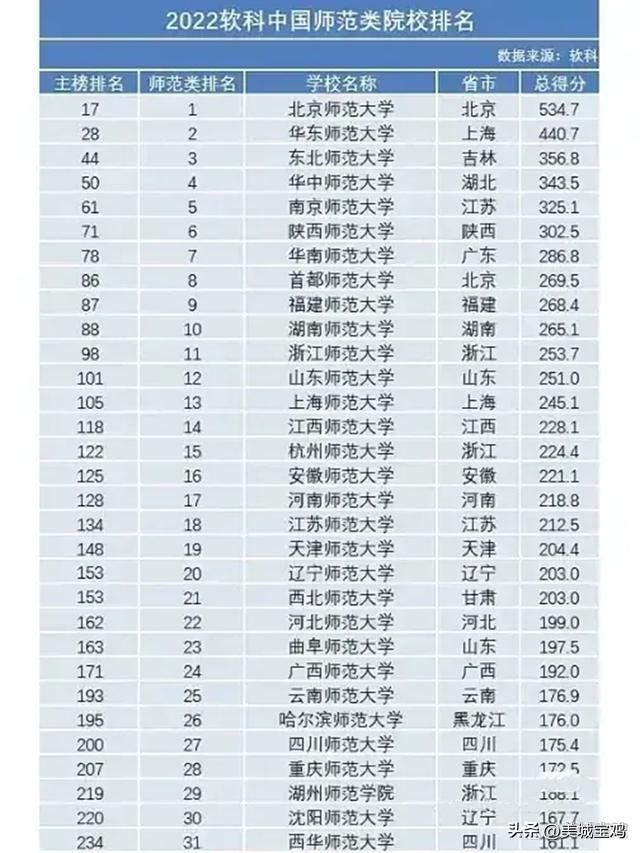徐州,地处黄河下游的黄淮平原,从古到今,至少经历过四五次人口大削减,第一次是东汉末年,第二次是五胡乱华,第三次是北宋灭亡,第四次是元朝灭亡,明朝灭亡算半次,每次人口灭亡后,原有的文化就被扫荡一空。
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区,黄淮平原的文物古迹遗存少得可怜,明朝以前的地面建筑和传统技艺寥寥可数,因此,这里的社会秩序都是极其脆弱的。
作为五省通衢,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历史上发生过四百多场大大小小的战争。近代以来的就有台儿庄会战、淮海战役等。
作为一座出过“十朝开国皇帝”、又是“五省通衢”的名声显赫的古城,徐州却从未做过任何封建王朝的都城,哪怕是陪都、行都,原因何在?
(十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魏文帝曹丕、南朝宋武帝刘裕、南唐烈祖李昪、齐太祖萧道成、梁高祖萧衍、吴越太祖钱镠、梁太祖朱温、南汉高祖刘陟、明太祖朱元璋。)
一是,徐州“地利”的安全性不够,地处黄淮海平原,“山川”低矮、交通便利,无天险可倚仗,近乎一马平川,易攻难守;
二是,徐州处于“树大招风”的南北、东西交通要地,黄河和淮河之间,战事频繁,北扼齐鲁、南屏江淮、西进中原、东观沧海,对于统帅名将来说,这里是理想的用兵动武之地,但对帝王来说,晚上睡觉都难以安稳,遑论定都久居?
三是,徐州的地理位置错过了不断迁移变化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历史上,我国的政治中心呈现出自西向东北转移到趋势(西安、洛阳、开封、北京,战乱时的南京、杭州是例外),经济中心是北方向东南方向转移的趋势(洛阳、扬州、苏州、长三角、珠三角),而徐州不南不北、不东不西的位置,次次与之失之交臂,历史给予他的定位是军事用途和交通要地的功能性城市定位,直到今天。
四是,古代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也是徐州无法定都的重要因素。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此地杀气太盛,非适合建都的祥瑞之地。据传朱元璋登基后,还专程派刘伯温赴徐州云龙山一带“断其龙脉”,破坏徐州的风水格局。
因此,江南富庶之地古来有之地“辛勤耕作/商业贸易—积累资金—增购田产”的发展模式在黄河下游行不通。
因为洪水过后,地貌大变,原有的地界、天界无影无踪,大家只能凭感觉重新划界,谁抢到就是谁的。
当人们见惯了财物易手,连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财产所有权都难以稳定维护时,人们对产权、人权能有多少尊重?
稳定的社会信用无法建立起来。洪水泛滥时,亲戚、朋友、债主、仇人,不是被洪水冲走,就是逃荒或迁居外地。
在极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模式会本能地选择短期策略、为了一点利益争个头破血流。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在苏北为官,他形容此处“土地荒芜,民惰而好斗,习于抢劫,故该地素称难治。”
我自小在徐州农村长大,耳濡目染,感受到老家民风之彪悍、乡情之粗野、行为举止之火药味,这从具有地域性格的语言上,也可以反应出来,比如:徐州方言用语简短、有力、刚劲——如两人一言不合动手,徐州人说“把他办了!”端起酒杯,普通话说“干了”,徐州人说“透”;答应朋友拜托自己帮忙时就一个字“ 管”;在扑克牌游戏“ 八十分”中,有一项规则,南方人叫“ 改主”,徐州人直接叫“ 反了”。
还有两个动词,远离故乡的游子,一听对方说,基本就能认同他是徐州人:“剋 kei”,这是徐州方言常用的一个口语词,一般做动词使用,有“快速做某事”或“凶猛野蛮地做某事”的意思,比较符合北方人豪爽的性格;“挒lie”,这个字含义极其广泛,可以作行动、打架、吃饭等解释,写为“犬文旁”得“犭列”,这个更显得彪悍,表现了徐州一带的民风。
老家农村民风之彪悍,集中体现在各大家族内外宅基地、巷口子、屋檐滴水处、门口道路等所属领地的纠纷上,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有时为了一块砖头的归属都能打得头破血流。家族和家族之间如此,家族内部也是如此。
小时候,见过村里彭家老大、老二为了屋檐滴水片瓦之地,亲兄弟打得不可开交,嫂子把小叔子的鼻子都生生咬下了一大块;赵家两妯娌为了一棵碗口粗杨树的归属,滚在地上打,浑身泥水,头发被撕扯得随风飘散;家族之间为了宅基地之间土台子,十几个人带着工具群殴,打累后,各家负责各家的伤员,一次解决不完,下次继续约架,有的甚至两大姓之间,结成了几十年的世仇;村与村之间,为了抢夺灌溉水资源,也时常爆发大规模的械斗。
我们所在的街东村,解放前是老镇东南片区,靠近曹氏小学、南吊桥和曹斜子地主大院,老住户主要由曹家的佃户、长工和雇工,铁匠、木匠、屠宰户、白铁铺、锔匠、裁缝、理发等手工业和服务业,在街里做各种生意买卖的商户和略有薄地的小地主构成。
几大姓的分布和家族行业大致如下:
曹家:以地主、近亲和帮工为主,解放后,时势逆转,被打压得抬不起头来,务农和建筑业为主,在村里所占人口最多;
魏家:以屠宰业为主,杀牛杀羊、在街里摆摊售卖;
刘家:祖传乡间大厨,解放前在地主家做饭,后在街里开饭店为主;
石家:打铁匠、打鱼、做豆腐为主,种地为辅;
彭家:以种地为主,街头小商贩
张家:建筑业、种地为主;
苗家:街里以小商贩和种地为主;
贾家:外来户,开厂开店、包鱼塘、包林地为主,爱钻营,改革开放的暴发户;
赵家:外来户,以服装生意为主;
吴家:外来户,村长、队长,镇政府有关系;
还有一些杂姓小户:韩、甘、李、张、葛等
我们石家祖上是清朝光绪年间,搬到镇上来的。高祖的三房儿子,一房住在吊桥北头、一房住在吊桥南头,一房住在北门。三兄弟以铁匠、打鱼、做豆腐为生,种地、短工为辅。我们住在吊桥南头的一大家子后面以铁匠和种地为主。
曾祖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爷爷老大,带着儿女以打铁谋生;闲暇时间帮人看风水、算红白喜事日子、木匠裱糊匠焗匠也会,克勤克俭,日子过得不错,搬到吊桥南头不久,就买下了一片曹家地主的土地,在上面盖了一处当时看起来比较宽敞院落。
当时,院子有五间堂屋、两间耳屋、两间厢房和一个过道间,一个大院子,门口就是一口大汪塘,连着东河长流水。院子一边靠街,一边靠路,还在南侧预留了半个院子大小的空地,是准备给二老爷成家盖房子的。
就因为这块空地,我们家和外来户贾家结下了半个世纪的“斗米恩升米仇”。
一九四一年,河南连续几年受灾,旱灾、水灾、蝗灾、疫灾迭至,当地老百姓纷纷外逃求生。驻马店的贾民国两口子一头挑着行李铺盖,一头挑着两岁的儿子,手牵着即将临盆的老婆,逃荒来到了八义集街里。
当时三口人衣着褴褛、形容枯槁、乞讨为生、见人就下跪,百般哀求换一点吃的,十分可怜。
三口人乞讨到了我们老院子门口,我奶奶看贾民国怀里的孩子,饿得都翻白眼,气若游丝,那时我三叔也一岁多,不由就动了恻隐之心,给了他们不少饭食衣物,他们跪倒连连磕头,千恩万谢。
后面几天,三口人又来我们老院子乞讨,几次三番哭诉,试探到我奶奶心软善良的性格后,贾民国哀求他老婆即将临盆里,能不能在老院子南侧空地搭个棚,暂时栖身,等孩子生完就走,求着求着声泪俱下。
我奶奶本来就没主意,一生谨小慎微,回屋请示祖奶奶,祖奶奶一辈子杀伐决断,打了一辈子苍鹰,没想到被贾民国这小子啄了眼。
他看贾民国一家三口,其状也惨、其言也善,也动了恻隐之心,同意他们三口人临时搭棚,但生完孩子、出了月子,就得拆棚走人。
祖奶奶一向心硬嘴刁、自诩识人善断,没想到错看了贾民国,给我们家带来了半个世纪的麻烦。
贾民国一开始非常谦卑,满脸堆笑地跑前跑后,帮着我们家院子打扫卫生、干干杂活,我奶奶也经常背着祖奶奶周济一下他们,尤其月子里,寒冬腊月的还把贾民国老婆孩子让进了厢房,帮着伺候了几个昼夜,他们当时也是感恩戴德。
当时,我祖爷爷和爷爷因为不愿意助纣为虐、帮日本人打制侵害国人的铁器,得罪了伪保长曹斜子,在外面跑反谋生活,不在家。院子里出来进去一个男子,多有不便。
后来出了月子,祖奶奶就不让他进门了,还是住旁边的窝棚,也没提赶他走的事情,奶奶还是常接济他家。
再后来,祖奶奶给他介绍到一个地主大院做个帮工,因为有我们家作保,地主也就收留了他,一日三餐无忧,一家人也就安顿下来了。
不得不说,环境改变人,艰难的环境更改变人。穷则思变。贾民国尝尽了饥饿的苦,体会到活着的不易,作为外来户 ,他没有什么倚仗的,只有溜须拍马的奉承、死心塌地的忠诚、一心为主的做派和察言观色的聪明,很快他就赢得了地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