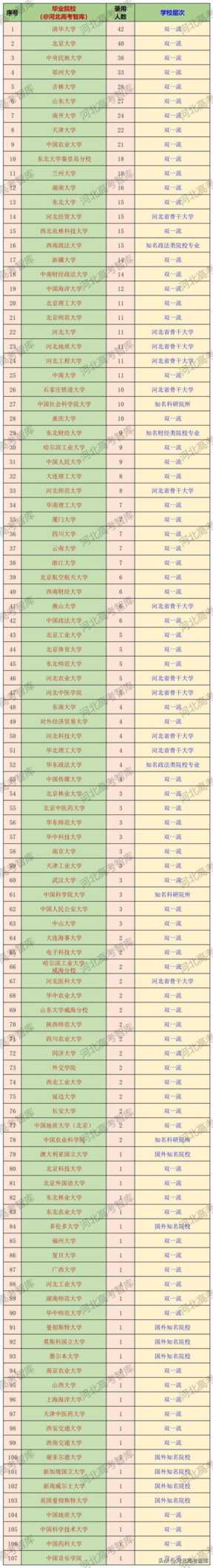© Williams Institute – UCLA
利维坦按:
区别对待是否合理,只在于评判体系是否成立。合理的区别对待叫因人制宜,反之则被斥为歧视。但是这样一个评判体系又该由谁来建立?怎么建立?是首要考虑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吗?还是首要考虑个体的基本需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势必不会足够简单。而且,当许许多多的个体被归为一个群体,这就成了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主题“discrimination”,更容易被直接翻译为中文的“歧视”一词,但这样的译法难免夹带了主观价值评价
(尽管在许多语境中不会是个问题,比如在讨论性别歧视的时候)
,因此在本文的多处我们会以“差别心”一词来取代,以着重于该词“区别化对待”的含义。

差别心(discrimination)是什么?人们在做道德选择时,也许会纳入某些不该纳入的考量。在差别心/歧视问题上,我们下意识会联想到种族或性取向,毕竟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们是黑人或同性恋而被禁止得到某些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年龄甚至也可以是影响道德决策的因素。比如孩子不被认为具备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因而不能拥有民主的投票权。
那么,我们如何决定什么是公平的差异化对待,什么是歧视呢?鉴定二者的标准又是什么?
个体说
一些哲学家说,歧视意味着对个体的不尊重。“个体性”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理论核心,因此“个体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密尔的观点。
“自我创造”是密尔派系功利主义的核心,只有理解了它才能明白个性之于歧视问题的关系。对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这位初代功利主义哲学家来说,不论是人类与否,每一个存在体都有着相同的价值。这样的出发点避开了“道德利己主义”的陷阱:因为我们同样重要,所以我不能把我的利益置于你的利益之上。

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 Literary Hub
但这种对善的定义导致的实际结果是——我们总是被要求帮助别人。迟早我们会感到被支配的倦怠,毕竟总有人过得比我更糟糕更需要帮助。
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当时出游的花销昂贵与不便,人们几乎没有机会去涉足那些远方的人的生活。而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影响他们,在如何帮助别人上也有很多选择。在道义上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人,但这么做的同时意味着放弃了个人的发展。
如果一个人每晚有三个小时的闲暇,那么为了将善最大化,他/她在道德上就有义务花这些时间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然而,那似乎阻碍了这些人发展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爱好。
我可能喜欢听爵士乐,并认为它陶冶着我的人格。当我选择在一个流浪汉收容所做志愿者,就没有时间去听爵士乐了。毕竟,我们已经假设我满足了生存需求,这里讨论的都是闲暇时光。功利主义声称我们应该将善最大化,所以它是在要求我们去帮助流浪汉而不是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
但这并不是说,我应该为别人牺牲我的个人发展。在功利主义中,人人平等。流浪汉的刚需比我的爱好更重要。我们应该最大化幸福,所以我们需要优先考虑他人的需求,次而考虑自己的欲望。
密尔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认为个性类似于音乐、美德,是个体成长的组成部分。但在进一步阐明个体成长的确切细节时,他则强调了“人类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密尔的个人主义有着一种深刻的人类中心意味,即人类的快乐高于动物的快乐。个性,指代一种知而后行的能力。密尔认为这是一种非人类动物不具备的能力。
© Smithsonian Magazine
有些人声称动物也可以被定义为个体。比如道德哲学家汤姆·里根(Tom Regan)曾说,如果从传记式的角度出发,动物确实是“生命的主体”,即它们不仅仅是活着,也在体验着生命。换言之,动物也需要去“成为”动物。
大多数动物拥有一种与树这样的植物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动物经历一些事情,其中那些满足了他们需求的事情对他们意义非凡。传记式的生活可以在质量上千差万别。毕竟生活的主体不只是像树一样只有需求,它还有索求和欲望。
有些事情对树来说可能客观上很重要,比如它需要阳光和水。但这些事情对树本身并不重要,它没有主观的生活。动物和我们的需求有所不同,但它们也同样有欲望。这些需求构成了权利的基础,而权利又构成了一种道德准则。就像人类一样,动物有生存的权利或拥有自由的权利(禁止工厂化养殖)。
© Campaign US
里根的观点不令人满意。既然我们有重新定义道德规范范围的能力,为什么还要半路把动物加入我们的定义里呢?后者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会把动物看作是我们自身的附加品。看看WASPI(全称为Women Against State Pension Inequality,是一个2015年成立的英国组织,旨在抗议国家养老基金在体制设立上的性别不公问题,译者注)妇女就知道这种方法的问题了。
这些女性声称英国政府操纵了女性的养老金,其在性别上的待遇不公构成了歧视。她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所在,比如女性辞掉工作抚养孩子的养老金总额要远低于男性。该组织主要目标是让人们注意到国家领取养老金年龄(SPA)的改变对女性造成的不公影响。
这一制度的运作起初主要为了满足男性的需求。它虽已经过调整以适应女性需要,但仍接连让人失望,这是因为当新问题出现时,它并不是以两性为中心来做出的调整。所以,重新建立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新系统上比中途改革要简单得多了。
坦白来讲,一些哲学家把动物纳入他们的人类中心理论的方式非常荒谬。比如在动物道德问题上,康德就有着臭名昭著的贬斥态度。康德系伦理学根基于“理性”,换言之,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是理性的。动物只是实验的饲料而已。对康德来说,对动物刻薄的人之所以不道德,也是因为这些人大概率对人类也刻薄。
克里斯汀·科斯加德(Christine Korsgaard)提出动物拥有一定程度的“最小理性”,希望以此将它们纳入康德伦理学。
她注意到猎物会意识到捕食者是在其他物体之间移动的生物,所以在避开捕食者视野范围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空间意识(某种初级的自我意识)。作为一位现代的康德主义者,科斯加德不想像康德那样把非人类的动物贬到道德低下的位置。毕竟对于康德来说,动物只是构成人类实践的道具罢了。
© Adam Dean
但为什么动物要像人一样才有重要性呢?我们应该因为它们本身的特性来肯定它们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它们与人类的相似程度。如果有人说女人像男人才有价值,或者有色人种像白人才有价值,那就太可笑了。
同理,乔尔·马科斯(Joel Marks)说:“就像人类不需要展示与其他动物的相似性来证明自身的内在价值那样,动物也并不需要。”
为什么猪要像人一样才能被纳入道德范围?为什么女人要像男人一样?马科斯为此公正断言道,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把相关性搞反了:不是说其他动物像人类一样才重要,而是说人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是动物。
权利说
非人类的动物似乎更符合权利说而不是个性说的伦理要求。许多非人类动物,尤其是那些我们食用的动物,似乎是有感知力的。
他们有着显而易见的需求(如充足的饮食)和显而易见的欲望(如社交或独立生活)。他们是有感情、有意识的存在体。虽然正如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除自身外是否存在意识那样,我们不能完全确定非人类的动物是否有意识。但它们看起来似乎是有意识的。
© NPR
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利是欲望和需要的表现,生命的权利和免受暴力的权利反映了求生和避痛的渴望。那为什么我们要把人类动物的权利置于非人类动物之上?
如果权利是欲望和需要的表现,那么人类动物和非人类动物都有生存的权利——他们都算得上是权利个体的单位。一个想吃动物的人固然有维持生命的权利。但是,人类不吃肉也能活着。而且很多证据表明,素食主义会非常健康。但如果人类选择吃掉非人类动物,他/她就侵犯了动物的生命权。这种观点建立在现代动物权利运动的基础之上。
多数情况下,差别心是在否定权利,但这也不能以偏概全。以权利来理解差别心存在几个问题:首先,权利讨论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对道德问题有指导意义。权利似乎可以成为我们对待非人类动物行为的规范指南。如果动物有生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吃它们。但我们人类经常把满足己欲放在动物的权利之上。
然而,虽然肉类对人并不是刚需,但它对类似于狗这样的食肉动物来说确实必不可少。杀鸡喂狗构成歧视吗?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在《绿色哲学》一书中给出了一个类似性质的道德模糊案例:
“猎场看守人必须保护环境和在这其中繁衍生息的动物。为了保护在地面筑巢的鸟类,他就必须对狐狸和獾加以管控。但动物权利活动家则要来这阻止一切的杀戮。最后猎物鸟也逃离了这里,猎场由食腐动物接管,成了一片管理不善的烂摊子。”
斯克鲁顿直言不讳地否定了动物权利保护的可行性。在这个话题上,他从不羞于表达自己的感受。但他确实说到了点子上。
© Bali Safari Park
基于权利的讨论并不能帮助我们制定一个权利的等级。如果我们声称所有动物都有生存的权利,那么我们如何管理一个由捕食者和猎物构成的生态系统呢?一些动物是以吃其他动物来生存的。如果我们因为猎物有生存的权利而阻止捕猎行为,那么我们就有完全可能在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
其次,这个说法存在着理论层面的问题。剥夺权利一定会构成歧视吗?当一个谋杀了其伴侣的女人被囚禁了,她可能失去了自由的权利。但是,这似乎又是一个公平差异化的例子。
这种说法的第三个问题是——道德权利的人类中心基础是不牢固的。什么样的人应该被授予权利?如果我们只允许人类拥有权利,我们就会面临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毕竟,在权利的争论中,对什么能被考虑进权利的范围尚未有明确的标准。
有些人认为只有人类具有理性,所以只有人类才有权利。但有些动物也拥有自主意识,比如黑猩猩。更何况,其实也只有部分人算得上理性。人类幼崽的理性也并未发育完全,那他们应该只被给予部分的道德权利吗?胎儿则只有拥有理性的可能性,毕竟它不太可能在子宫里形成道德准则。还有那些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人呢?他们不再值得被纳入道德考量了吗?
© Tenor
乔尔·费因伯格(Joel Feinberg)在堕胎辩论上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论点。对他来说,拥有一项权利的可能性并不直接意味着获得了该权利。所有18岁以上且未被监禁的英国居民都有可能成为首相。但首相只能有一个人。
我可能有成为母亲的潜力,母亲也可能有产假的权利。但我不能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就任意在公司要求产假。
我们所谈论的这些角度,都在试图借鉴“权利”、以理性为中心的“个性”这些人类向的概念。我们这里研究的理论都基于非人类动物或有或无的某些能力,而不是它们真正做了什么。
充分性和必要性
不尊重某些人的个性或否认他们的权利,是构成差别心(歧视)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举个例子。试想,一个性别歧视的法律制定者声称女性应该待在家里。他想禁止女性进入“公共空间”,一种既不尊重女性个性又侵犯了自由权的行为。然而,这只满足了歧视的充分不必要前提。
语境的相关性
这些关于歧视的历史描述只触及了问题的表面,未能解释为什么当下的一些事件是错误的。同样,马戏团动物表演的不道德不仅仅是因为它违背自然,问题远非如此。
自然主义的谬论
当代人的生活明显不同于我们祖先的生活。但这意味着都市生活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吗?表演马戏戏法的熊从大自然被带到人工环境中,但人类也同样经历了环境迁徙。我们原先打猎采果,后来开始了农耕,但现在却生活在一个机械化的社会里。
我们把熊从它的自然环境中带出来了,但这并不一定是错的。毕竟像野火或自然灾害发生,环境变得有害或危险时,许多动物都会被带离它们的环境。
同样,给动物穿衣服也不是根本性上的错误——有些宠物可能确实需要特定的衣服。犬类抗焦虑衬衫可以通过紧抱住狗来帮助它们镇静地度过篝火之夜等紧张情况。如果飞机失事落入海洋,给狗穿上救生衣也是正确的。
具体情况决定了给动物穿衣的道德性。在这些案例上,也体现了道德取决于语境的这一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剥夺权利可能并不构成歧视,比如犯了滔天罪行被剥夺自由权的妇女是受到公平差异化对待的。判断是歧视性差异化还是公平差异化还是要取决于具体语境。
《波士顿环球报》
一个典型例子是发生在波士顿地区,一起众牧师性侵儿童和年轻人的丑闻。《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将看似孤立的性虐待案件,与该地区神父们迅速转移到其他教区以逃避司法审判的“神秘失踪”联系在一起。
像其他公民一样,天主教牧师当然也享有保留隐私和平静度日的权利。然而,阻止犯罪优先于保护隐私权。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确实存在权利的等级,但这些权利在等级中是流动且取决于语境的。
由于他们罪行的本质和对职权的滥用,波士顿神父失去了拥有私生活的权利。但如果仅因为牧师自我认同是男性或天主教徒就剥夺他们的隐私权,那就又将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与当前问题无关的特征上了。
外星人的例子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外星人造访地球的可能性。对这些外星人来说,人类是最美味的食物。外星人认为他们的心灵感应能力使他们优于人类动物,那他们为什么不吃我们呢?【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人类的偏见》(The Human Prejudice)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好吧,我们可能会认为外星人有心灵感应是件好事。我们甚至会嫉妒他们。这并不是说心灵感应能力本身不好,而是这些能力不能决定我们的道德价值。我们还是不应该被吃掉。对道德而言,重要的是某一特性或所处的环境,而不是能力本身。

© FES Connect
心灵感应不是道德价值的基础。我们不曾拥有过这项能力,它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的内在价值是因为我们珍惜自己的生命。人类可能没有心灵感应的能力,但这和他/她自己的意识经验无关。
因为一种生物不会心灵感应就决定吃掉它们,这会构成一种歧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吃动物,就因为它们缺乏理性吗?杰里米·边沁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他说:“问题不是 ‘它们会推理逻辑吗’,也不是 ‘它们会说话吗’,而是 ‘它们会受苦吗’。”
当有人认为女性应该被限制在私人领域时,他们考虑的因素是如性别这样与公共领域表现能力无关的东西。同样地,关注一种生物腿的数量,语言能力,或社会生活能力,都是与道德立场无关的事情。
在具体语境下,年龄等因素可能是判断公平差异化或歧视的基础。很难想象基于种族的歧视,会构成公平差异化的案例。也许考虑到COVID-19对有色人种患者的影响远比白人严重,我们应该优先治疗有色人种患者而不是白人患者。
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一个10岁的孩子不应该有投票权,但年龄本身不应该构成他们获得公正的障碍。这并不是说考量年龄本身是错误的,而是在应对当前的问题时,我们考量的是否是一个恰当且可以缓轻现态的因素。
如何在语境中确定某个因素的相关性呢?难点就在于此。一些哲学家说,物种是一个相关因素,但对我来说那不是。回想到边沁的话,我相信的是我们不应该伤害那些会受苦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