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殖民政府从1897年开始将台湾少数民族的团体带往日本。在1911、1912、1928、1925、1928、1929年,以及从1934年到1941年的每一年间,都有这样的团体从台湾前往日本。而从1915年——日本在这一年宣布领有赤道以北的原属德国的密克罗尼西亚殖民地——开始直到1939年,南洋的海岛居民每年都被带往日本。这些团体的旅行一开始是由日本海军、后来则由拓务省组织。在这些旅行前后跨越的大约四十年时间中,它们的意义随着帝国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1930年代末以前,它们促进了一些团体成员被同化为日本忠实的殖民地臣民,因而被认为是成功的。不过,从广泛的角度来看,以宗主国旅行为背景发生的接触引发了殖民地臣民、组织这些旅行的官员,以及宗主国大众之间的各种不一致的阐释,对日本帝国近代性范围内文明与野蛮的定义和边界提出了质疑,而不是巩固了关于帝国的统一的叙述。

《入京生藩观光团一行》(《入京せる生蕃観光団》),美术明信片,1910年代(出自陈宗仁编,《世纪容颜(上)——
百年前的台湾少数民族图像》,台湾图书馆,2003)
1912年台湾人旅行的记录显示,这个团体在东京一共呆了八天。在整个旅程中都有警察与他们同行。这些官方组织的旅行并不是使节团出使——除了总督府和拓务局(后来的拓务省)代表的象征性的讲话,它们并不包括谒见皇室或与高官会面。它们也不是休闲旅行:至少在早期的旅行之中有着高度的强制性。并且,这些团体被带去的场所都有着压倒性的军事性质,1912年的团体在第一天首先就被带去了一个大炮工厂、一个子弹工厂和一个军械库。这个团体还参观了二重桥、浅草的两个剧院、上野动物园、拓殖博览会以及白木屋百货店。他们并没有参观诸如帝国剧场和帝国饭店这样的上流资产阶级的文化地标。

《生藩人观看陆军步兵操练》(《生蕃人陸軍歩兵操練ヲ見ル》),美术明信片,1910年代(出自陈宗仁编,《世纪容颜(上)——百年前的台湾少数民族图像》,台湾图书馆,2003)

《(台湾藩人观光团)东京士官学校加农炮射击实况》(《(台湾蕃人観光団)東京士官学校加農砲射撃の実況》),美术明信片,20世纪最初十年
1912年的另一个团体的一位随团警官对这些旅行者的印象进行了摘要记录。与所有宣称代表了处于殖民统治下的人们的言辞和感想的文件一样,这份报告也必须被当成高度加工过的信息来对待,其中有关作者与预期读者的内容与有关殖民地臣民自身的内容一样多。尽管如此,它还是让我们能够一瞥台湾团体对日本主人试图教育他们、同时威吓他们的努力的感受。考虑到旅行的日程,这份摘要的相当部分很自然地都在描述这个团体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所形成的印象。即使是在他们被带去的学校,年幼的学生们也在“研习战争学问”。不过,这个团体的印象并不只是基于日本在制度或技术上的优越性;这些人显然单纯被东京无处不在的士兵的数量所震撼。在报告书中,他们这样说:“所到之处均布有军队,其数目终非自己所能计算。”
然而,我们很难确定这样的军事力量展示达到了威吓这些观光者的预期效果。1912年5月15号的《台湾日日新闻》报道了他们对靖国神社的访问。这个团体被带去参观游就馆,据这家报纸所说,“他们在馆内转了一圈,看到一把名刀后厚脸皮地说‘傻瓜才会把这种东西藏起来,这么锋利的刀起码该给我们一把’”。这种语气看起来不像是出自畏惧之人之口。游就馆中展示的可以使用的武器肯定不仅让这些台湾少数民族访客想到了日本的军事优越性,而且让他们想到自己被迫不带武器来到东京。
将帝国首都展示为充满武器和士兵的场所所带来的讽刺性效果早在第一次来东京的台湾团体的反应中就已经很明显了。据报道,一位报纸记者曾问1897年的团体领袖泰牟?米塞鲁他为何要参加这次旅行。泰牟?米塞鲁列出了两个理由:首先,他听说日本人都是没有工作技能的小偷,所以他想看看在日本是否有人耕田;第二,他的族人被禁止持有枪支和火药,因而他打算要求日本方面取消这一禁令,以使自己人不必再被迫去违法购买它们。在日本期间,无论走到哪里,泰牟?米塞鲁的团体都要求主人给他们枪。在他们即将返回台湾时,泰牟?米塞鲁向一个译员表达了自己的沮丧,他的话被记录如下:
在我们出发时,总督府中有一个头领告诉我们:“你们要放弃猎取人头的做法。日本人当初也和你们一样,但后来我们发现了这样做的坏处,互相沟通和睦,因而如今房屋、道路等等都万事齐备。你们也应该赶快停止猎取人头,努力做到跟日本一样。”然而当我们来到日本后,发现道路房屋确实很漂亮,但同时日本却在大量生产步枪以及大炮弹药。在和平时期为什么要急着到处生产武器呢?日本人又给我们看了从清朝俘获的大炮,自豪地告诉我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但我却想不通为什么日本人生产了这么多的武器,却只分配给自己的部下,而不让我们买卖它们。
在他们回到台湾后,台湾总督在台北亲自接待了他们,并送给他们每人一把仪式性的日本刀。他们直截地拒绝了这些礼物,说它们不顶用(记录下的原话是“这些刀连头野猪都杀不死”)。译员一再催促他们接受这些刀作为访问日本的纪念,他们最终也这样做了。但当离开台北的火车晚点时,他们因此而恼怒,扔掉了这些礼物并步行踏上了回家的道路。以日本在武器方面的强大来给这些访问者留下印象、并让他们屈从的做法起到了反效果,只给他们留下了关于殖民者自私的印象。
在帝国首都,最令这些来访者感到害怕的不是军事力量的展示,而是与当地人群的接触。1912年来访的团体在浅草被看热闹的人围观,而警察的报告书中描述说台湾少数民族民众对那些保护自己免于受伤的随行人员十分感激。一段可能出自观光团员或是随行人员之口的启示性的评论这样总结这段插曲:“我们所到之处,内地人即群集而来,好像是想要看我们身上的奇异的服装以及脸上的刺青。”即使在那些看热闹的人群被隔开一定距离的地方,这些少数民族民众也知道自己在被围观和报道,并且肯定持续感觉到了那些“内地人”(日本大众)观看自己的目光。对于前来观光的台湾少数民族民众来说,这种对自己受到大群内地人注视的自觉与帝都向他们展示的各种奇景、以及围观的人群自身——台湾少数民族民众的叙述中描述称他们多得“像蚂蚁一样”——有着同样深远的影响。在大约二十年之后的1935年,一个回到台湾的观光团被要求向他们的同胞进行公开的演讲,其中一些人说到了当内地人盯着他们脸上的刺青并问他们从哪里来,还表达了希望他们在台北的医院里去掉这些刺青的愿望时所感觉到的屈辱。从1910年代开始,台湾当局就在试图根绝刺青,但当地的风俗顽强地残留了下来。据193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48%的泰雅人有刺青,而在三十岁以上的人中这一比例更高。1940年8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到当时为止,台湾少数民族中共有72名男子和23名女子通过手术去除了刺青。在帝国内接触史上的某个时点,在家乡会是最大骄傲的身体记号成为了一种耻辱。

《入京生藩观光团五十二名一行(泰雅族四十社之头目)》(《入京せる生蕃観光団五十二名一行(タイヤル族四十社の頭目)》),美术明信片,1910年代。在图中女性所撑的伞背后可以看到被拥挤的人群包围着向前行走的台湾观光团员(出自陈宗仁编,《世纪容颜(上)——百年前的台湾少数民族图像》,台湾图书馆,2003)。
接下来这幅图片并非某个观光团的照片,但其中拍摄的是可能成为了观光旅行的主人和客人的人们。照片拍摄于1920年代一次反殖民运动被镇压之后某个时期的台湾。日本警察利用殖民化的台湾少数民族部落来攻击那些抵抗殖民统治的人们。在宗主国,这些台湾少数民族客人们所看到的官方象征语汇并没有公开展示对被征服者的杀戮或是羞辱。不过,展示割下的人头的确是日本与台湾的武士们共通的悠久传统。1860年代到访日本的西方人看到罪犯的人头被砍下来穿在通往首都的大道旁边的桩子上。尽管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废除了将罪犯斩首的做法而代之以西方式的绞刑,但军队中仍然继续对非日本人进行斩首。而砍下的头颅继续在日本本国的大众文化中广为流行。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俘获的武器在东京进行了展示,但如同木下直之所写到的,民众很显然想要看到人头。甲午战争之后的胜利游行中出现了做成中国人的人头形状的灯笼。展示人头这一最近的——或者说当时依然活着的——日本传统使得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成为迷恋和忧虑的特殊对象。在创办于1932年1月、面向殖民地官员和警察的《理蕃之友》(《理蕃の友》)杂志的第一期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讨论了台湾猎取人头的做法,并极力将其与日本武士的“勇壮”行为区别开来。这位作者解释说,日本武士在砍掉敌人的头时会报上姓名,而不是偷偷地袭击。1936年的台湾观光团(其中包括两名妇女)曾被乡下的旅馆拒绝入住,因为旅馆主人害怕自己的头会在夜里被砍掉。

日本警察、泰雅族等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等警察所谓的“友蕃”以及他们受日本统治者所托杀死的萨拉矛社、斯卡谣社等“敌蕃”的首级在雾社支厅拍摄的纪念照,1920年左右(台中市林志诚藏,台湾东亚历史资源交流协会修复)
在1920年代末,台湾人的宗主国观光的特征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日本主人和台湾客人都开始为对方戴上和平文明的面具。到此时为止,台湾的殖民统治已经持续了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少数民族的子女在学校里学习日语。如同保罗·巴克利(Paul Barclay)所详述的,在殖民当局的鼓励下,一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女儿被许配给日本警官,以结成策略性的同盟。据报道,1928年的第九次台湾观光团自己支付了旅行费用。1929年,台湾观光团穿着青年团的卡其色制服来到了日本。而从这时起,他们旅程中的重点也从军事设施变为以皇宫为首的标准的皇家场所,以及一些文化设施。比如,1935年的第十一次观光团的旅程中首先有皇宫,然后是拓务省、台湾总督府东京事务所、《朝日新闻》报社、明治神宫、靖国神社及游就馆、上野东照宫、市内的各种景点、动物园、地铁、浅草、三越百货店以及银座的夜景。几次观光旅行的记录中还提到了由一位在台湾拥有事业的企业家赞助的、在著名的雅叙园举行的奢侈的宴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是受到同化的少数民族年轻精英男性以及担任他们随行人员的殖民地警察的公款游玩。内地观光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变成现代意义上的“旅游”。

1935年4月20日,第十一次台湾少数民族“内地”观光团(泰雅族与布农族加起来共三十人)在从台北出发前参拜台湾神社。据《理蕃之友》所说,此次内地观光报名者甚多,“为避免浪费金钱”,只有青年团部长等“中坚人物”被选拔入团(出自《理蕃之友》1935年5月号)。
这并不是说殖民地和宗主国如今都已处于和平之中,1930年代初的宗主国报纸读者们对这一点都很清楚。在1930至1933年间——这是第九次和第十次观光旅行之间的一段空白期——发生了许多著名的暴力事件。在1930年10月的第一次雾社事件中,赛德克族人的一支游击队袭击了警察的枪械库夺取武器,并攻击一场学校运动会上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的人群,共杀死134人。他们的领袖莫那·鲁道曾参加过一次前往日本的观光旅行。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日本军警杀死了644名赛德克人以作为报复。而在东京,1930年11月,滨口雄幸首相受到一名极端民族主义者枪击,后因此而死。接下来在1931年4月发生了第二次雾社事件,与日本殖民政府结盟的台湾少数民族士兵屠杀了被关在一个日本收容所中的所有幸存的赛德克男性。关于这次屠杀的报道最终迫使台湾总督太田正弘于1932年3月辞职(在此之前,宗主国的报纸读者主要被关东军的活动以及伪满洲国的建立所吸引)。1932年5月,一群日本海军军官闯入犬养毅首相在东京的宅邸并将其枪杀。他们还试图杀死另外几个公共人物,并且计划杀死正在访问日本的卓别林。尽管这些在台湾山地和宗主国首都中心发生的事件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们在同一时期内的连续发生让人们意识到,尽管有着官方所宣称的文明化和帝国近代性的绥靖效果,但两个地方受到疏隔和心怀不满的人们仍然持续地倒向针对平民和文官的武装暴力行动。
到官方正式发动在殖民地民众中培养忠诚的帝国臣民的“皇民化”运动的1937年,《理蕃之友》中关于宗主国之旅的报道已经成为一种帝国巡礼的陈词滥调。旅行的组织者们汇报他们手上的旅行人员举止多么地规矩,他们怎样在看到二重桥后流下眼泪并唱起国歌,而一些旅行者则(在台湾的警察局举行的旅行归来集会上)报告了自己对于能被带往神圣宗主国而感到的敬畏、感激和自豪。讽刺的是,杂志中提到的仅有的一个例外是一名平地少数民族——比起山地少数民族来应当更加“文明”——雅美族的成员,并且还曾接受过六年的正规教育。在回到台北后被一名殖民官员询问时,这位雅美族旅行者简单地回答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农场、火车、八幡制铁所,以及宗主国大米的质量。他既没有提到帝国纪念物,也没有提到尊崇或是敬畏的感情。与同化那些没有拿起武器反抗殖民者的少数民族的尝试相比,殖民地警察对山地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深度参与以及宗主国威慑这些更富于反抗性的人们的努力或许最终成功地在他们与帝国之间建立起了更强的联系。即使在双方之间的关系最为和平的时候,通过帝国首都传递帝国威严的努力也从没有与武力威胁完全分离。
1940年,《理蕃之友》上第一次刊登了一幅观光团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拍摄的照片。这幅照片很明显是在当年五月份的观光旅行期间拍摄的。或许到了这个比较晚的时候,组织者们开始暗示将来的参政权,以换取这些少数民族民众的忠诚。但讽刺的是,到了当年的10月,国会中的所有政党都被解散并合并进法西斯主义组织大政翼赞会,战前日本的代议政制实验就此终结。即使到了这一阶段,少数民族的观光日程安排依然在将帝国首都展示为一个政治首都的同时亦将其展示为一个军事首都。而一群群被带到东京的学童的旅行日程也是如此,他们在参观靖国神社之后还要遍访古代和近代军事英雄的公共塑像。这些塑像是帝国近代性的国际语汇的一部分,它们之中有许多在日本帝国崩溃后都没能存留下来。1945年以后,美国的占领当局销毁了一部分这些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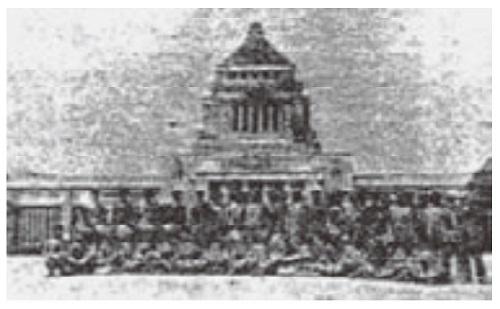
在帝国议会议事堂前拍摄纪念照的台湾少数民族日本观光团(出自《理蕃之友》1940年6月号)






